【散文】 童年老屋
我出生在吉林东北一个并不富裕的小村屯,那时家家几乎都是茅草房。屯子不大,人口却密,红砖房是见不到的,能有三两户黑砖房,已是屯里数得着的体面人家。
我就是在一间普通的茅草房里长大的。母亲总说,我出生时的待遇算“特殊”——她是搭着队里的马车,去乡里的卫生院生的我。那卫生院是乡里少有的红砖房,气派得很,可我那时什么都不懂,自然体会不到这份 “优越”。母亲说,卫生院住一晚要花不少钱,所以我刚在产房里发出几声啼哭,就被抱回了老屋。产房没在我记忆里留下半点印记,童年的所有画面,都装着老屋的模样。
我家的老屋是两间矮小的茅草房,墙是土坯砌的,房顶盖着厚厚的稻草。小时候最怕阴雨天,总担心雨水浸透茅草漏进屋里,浇湿粮食和被褥。可神奇的是,这份担忧从来没成真过,稻草顶像层紧实的铠甲,护着屋里的日子。
老屋的入户门是东院二爷送的,是他家替换下来的木质板门,看着旧,却结实得很。二爷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,谁家孩子结婚想找他打家具,得提前一个月上门预定才排得上号。他摸着门板说:“这木头好,再用二十年都坏不了。”或许是因为和二爷家东西院住着,处得亲厚,我们才能在亲戚里“近水楼台”,得到这扇抢手的门。
踏进门就是厨房,空荡荡的,只有一个简易的木质碗架,和一口黑铁锅。那口锅在我眼里曾是“魔法道具”——母亲总能用它烙出各式美味的饼:鸡蛋葱油饼咬着脆香,糖饼甜而不腻,苏子黏饼软糯带劲。那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,一想起来就忍不住咽口水。可一年到头,这样的饼也就能吃上三两回,其余时候,锅里多是炖萝卜条、土豆条或酸菜汤,我总忍不住抱怨母亲“舍不得用锅”。
再往里就是睡觉的地方,一铺大火炕占了半间屋,上面铺着张用了多年的高粱秸秆编制的炕席。不换不是用不坏,而是舍不得。炕面看着凹凸不平,躺上去却软乎乎的——炕席底下铺着厚厚的稻草。那时候农村没有床,更不知道什么是席梦思,却独独念着火炕的好。尤其是寒冬腊月,大锅一烧,炕就热了,外面寒风刺骨,钻进被窝的瞬间,浑身都被暖意裹住,幸福感能溢出来,那舒坦劲儿,后来再没找着过。
里屋没什么像样的家具,只有两只向上翻盖的厢式柜子立在靠西侧的墙边,一边搭在炕沿上,另一头靠木方子支撑,好让其与炕的高度持平,下面还会围一圈碎花布,即可遮丑,又可储物。可别小瞧了这两只柜子,那可是父母分家时分到的唯一大物件,在我眼里更像“魔法箱”:一到过年,父母总能从柜子里“变”出东西——有时是一把发软的糖块,有时是几个皱了皮的国光苹果。可等我再去翻找,却什么都没有,但仍然会把头伸进柜子里,狠狠地嗅一嗅糖果和苹果留下的余香,勾着我盼了又盼。
让我记忆最深的是,有一次我感冒发烧,吃了药,却一连两三天都不退烧,整天迷迷糊糊的,吃饭也没有胃口,父亲竟然从柜子里“变”出一盒康师傅桶装面,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那样高级包装的方便面,味道真是美极了,如同吃到了山珍海味,我甚至把面汤都喝得滴水不剩,就连吃过的面桶都没舍得扔,把它当做日用饭碗,直到最后彻底垮掉。神奇的是,我的病居然很快就好了,真不知道是不是那盒“昂贵”的桶装面起了大作用。
屋内的地面是用黄土铺的,原本还算平坦,却被我们几个小伙伴挖了不少小坑,用来弹玻璃球。玩到兴头上,还会在地上翻跟头、抱摔,自然会少不了被大人呵斥,即便弄得灰头土脸,却仍快乐无穷。
这栋茅草房子看起来很小,窗户也不大,南面两扇,北面一扇,都是向上翻开的样式。夏天天热,不管家里有没有人,都会用木棍把窗户支起来通风——不用怕进贼,家里实在没什么值得偷的。前后窗一开,过堂风穿屋而过,比现在的空调还舒服。到了冬天,就得提前打浆糊,用报纸仔细把窗户缝糊上,免得漏风。后来条件好些了,会多加一层塑料布,保暖效果更好,还省柴火。
那时很多人家都没有电视,没什么娱乐,但也不会太早钻被窝。晚饭后,三五家的会凑到一起唠闲嗑,东院二爷家就是最热闹的据点。他家里有个小火盆,每天都烧得热乎乎的。我们一家四口几乎每晚都去,大人们通常都围着火盆烤手,有时说说笑笑,有时却谁也不吱声,只是静坐,偶尔会被二奶连续敲打烟袋锅的声音打破沉静。我们这帮孩子,就借着微弱的月光在地上摸黑弹玻璃球。赶上幸运的时候,大人们会从火盆里翻出几个烧土豆,外皮焦脆,里面粉糯,那香味,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馋。通常要到天黑透了,大家才散伙回家。我一进门,立马扒掉棉袄棉裤钻进暖和的被窝。有时会在进屋前从窗户下的大缸里,顺手捡两个粘豆包或者冻梨,裹着棉被啃完,便美美得一觉睡到天亮。
每逢过小年前后,老屋都要经历几番必不可少的“装扮”——扫房、裱墙、贴窗花。先找根长木棍绑上笤帚,把屋顶墙角的灰尘扫得干干净净,然后会在窗户上贴上几张母亲亲手剪制的漂亮窗花,再用报纸和好看的挂历抹上浆糊,把屋内的墙面和顶棚裱得亮堂堂的。说起顶棚,就想起母亲讲的,当初买老屋的往事。
家里除了我,还有个大我七岁的哥哥。母亲说,哥哥出生时的条件,比我差远了。父亲兄弟姐妹多,五个兄弟三个姐妹,他排行老三。父母结婚时,大姑和大爷早已成家,因为爷爷家不富裕,所以并没有自己单独的房子,只能借住在大爷家。
大爷家也只是两间小草房,一个厨房一个卧房。为了少些生活上的尴尬,大爷和父亲在屋子北面搭了个小北炕,晚上用布帘隔开,哥哥就是在那座小北炕出生的。后来两家人三个孩子挤在一起,实在不方便,父亲就拿出所有积蓄,从屯邻手里买下了这栋老屋。母亲说,当时的房子破得很,墙体掉了皮,里屋的屋顶是裸着的,抬头就能看见木架子,结的蜘蛛网被四处漏的风吹得晃来晃去。可即便这样,搬进去的第一晚,一家人却睡得从未有过的踏实。
第二天姥姥来了,看见屋顶的模样,红了眼圈。走的时候,她硬是塞给母亲五毛钱,嘱咐父亲:“去乡里买些大白纸,把棚顶裱了,大人能将就,孩子小,可受不住这风。”还好那时是初秋,天不算冷。父亲拿着姥姥给的五毛钱买了大白纸,又找了几个帮手,用了两天时间,把屋顶和外墙面修修补补、裱糊一新,老屋这才真正有了“家”的样子。
母亲常说,那时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小窝,一家人就觉得满足得很。她总逗我:“你最该感谢老房子,要是没它,说不定就没生你的念头了。” 就是在这样的老屋里,在满是烟火气的日子里,我被安安稳稳地孕育,快快乐乐的长大。
父母对待生活,既肯吃苦,又有奔头,除了照料自家的一亩三分地,还总想着挣些外快。每逢农忙时,急匆匆干完自家的地,再到别家去赚手工。通常是白天在地里忙了一整天,晚饭后还要披着月光再回到地里,一干就是大半夜。赶上阴天没月亮,就凌晨三四点起来,迎着朦胧的晨辉起早干。靠着这份勤快,没几年,我们家就在老屋东侧盖起了一间红砖瓦房——那时候,这在屯里还是稀罕物。可新房盖好后,却一直当仓房用,直到后来拆了,也没住过一天。我曾满是疑惑地问母亲:“为啥盖了新房却不搬进去?”母亲笑着告诉我:“等你和哥哥都长大结婚了,再住进去。”从此,我便天天盼着自己能快点长大。
后来才懂,那新房虽看着有模有样,屋顶也砌了烟囱,可离能住人的标准还差得远——屋里并没砌间壁墙,也没搭灶台和火炕,更别提添置家具了。或许那时父母的钱,只能够撑起个房屋的架子,就像当初买老屋时,只有房壳子,没有像样的顶棚一样。
从那以后,父母更拼了,哥哥也在初三那年,瞒着家里辍了学。中考前两个月,他每天还装模作样背着书包出门,其实是跟着邻屯的姑父去修路挣钱。父母早出晚归,竟一直没发现。直到中考结束,哥哥把两个月挣的钱递到父母面前,家里才知道他没参加考试。母亲问哥哥为什么瞒着家里不去上学,哥哥只是低着头,喃喃的回了一句:“就是不想念了,想下地干活帮家里挣钱。”母亲听后没有责备他,只是沉默了半晌。父亲坐在西炕沿边,肩膀依靠着炕柜,眉头紧锁的低着头没有做声。家里从此多了个能扛事的苦劳力。
终于,在我十岁那年,也就是1996年,我们家成了屯里第二批盖起大瓦房的人家。当时屯里只有在乡里当副乡长家、他家开拖拉机的弟弟、小队的队长家和开磨米厂的大爷家盖了瓦房,我们家能盖房,靠的是父母起早贪黑种地干杂活、哥哥辍学修路挣钱的结果,这在当时的农村,是“勤快人家”的象征。
我们家的新房不仅有两个卧房,中间还留了间大客厅,棚顶做了新潮的造型,金色的胶条配着五颜六色的金片,看着格外“高大上”。厨房和餐厅也是分开的,算下来,一共七扇门,三间屋子,两个厨房,一个餐厅,可比老屋宽敞多了。
就这样,老屋和之前盖的小瓦房,在盖新房前一起被拆了。我记得拆房子那天,父亲起得特别早,围着两座老房子转了好几圈,手时不时摸一下土坯墙,不知道在眷恋什么。可我那时却急着盼着它们快点被拆,满心想的都是住进新房的新鲜劲儿。
如今我窝在城市十几层的密封窗后,地热烘得空气发燥,空调风裹着粉尘——这是九十年代的老屋从不会有的“体面”。那年拆老屋时,父亲摸着土坯墙发怔,我却急着往新房跑;如今再想起,才懂那土坯墙里嵌的不只是我的童年,是东北乡村从茅草房到红砖房再到高楼的三十年:是父母攥着汗珠子换的“安稳”,是哥哥辍学撑起的“体面”,是整个村子从“凑着过”到“奔着活”的细碎褶皱。老屋倒了,可它矮檐下的温度,早成了我揣在城市里的“坐标系”——后来所有的“往上走”,都在丈量和那代人“踏实活”的距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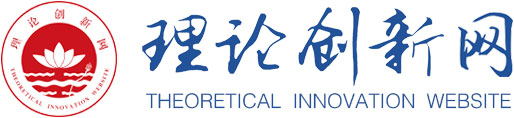
 鲁公网安备37010402441507号
鲁公网安备37010402441507号